熊钿|万物有名:汉唐间动物命名问题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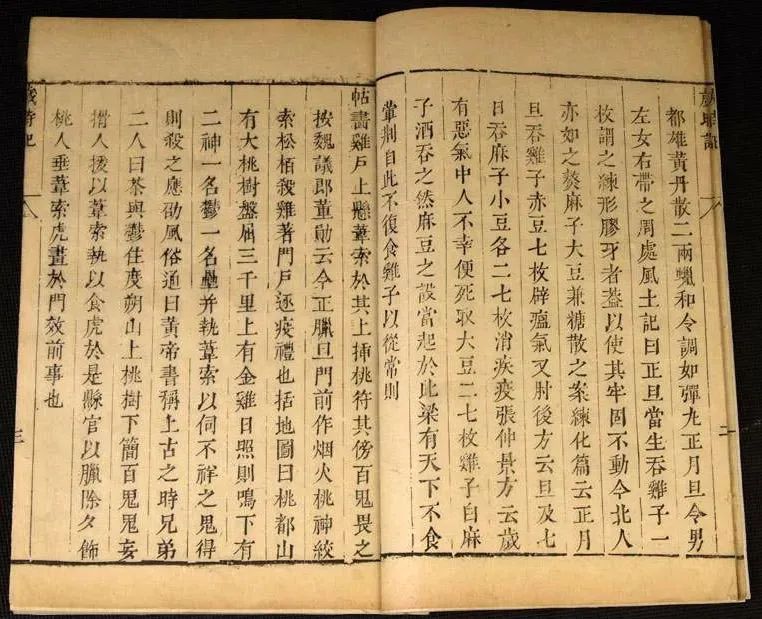
“名,明也,名实使分明也。”万事万物皆有名,命名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最初一步,也是厘清宇宙天地的重要一环。如尧在位时,派诸官分掌各事,“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种,农殖嘉谷”,其中,大禹治理水土,命名山川,通过命名强化对自然和政治秩序的控制,从而将命名从认识自然上升到政治统治的高度。
命名源于何时,如何建立名与实的对应关系,是一个充满思辨性的话题。本文无意探讨诸如“马”何以为“马”或“白马非马”之类的哲学问题,而是将论述重点放在动物命名方式本身及其演变上。命名具有时空性特征,故不可脱离历史语境去空谈命名问题。
荀子曾在《正名篇》中对世间万物的命名原则进行了概括,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包括动物在内的世上万物之间都存在同、异现象,“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第二,“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能够用单名说明的使用单名即可,如牛、马等;单名不足以说明的则用复名,如水牛、白马之类。第三,“名无固宜”“名无固实”,事物的名称无所谓适宜与否,只要约定俗成即可。第四,事物形状相同但本质不同,为两种实体;形状不同而本质相同,则为一种实体,需要仔细辨别。
命名产生于“识物”过程,与人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虽然荀子提炼出命名基本规律,但在实践中问题要复杂得多。关于动物命名,学界多有研究,如李海霞《汉语动物命名研究》是较早从语言学角度分析动物命名原则的专著,所论颇有启发,但因时代跨度较大,对中古这一时段的讨论不够细致。胡司德在《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一书中亦谈及动物命名话题,其对字书的强调为动物命名研究提示了线索与突破口,可惜所论仅限汉代,对此后中古时期动物知识的变化并未涉及。
汉唐时期,地理版图扩展、中外交流频繁,大量域外动物或动物知识传入,拓宽了认知视野;再加之炫博求异类著作大量出现,留下丰富的动物史资料,为讨论动物命名问题提供了可能。先民通过何种方式为动物命名?不同时空条件下动物名有何不同?知识结构和学术风气流变又如何影响动物命名?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本文力图另辟蹊径,对以上问题尝试做出一些新的思考。
一、“象音”与“会意”:两种古代动物之命名法
古代精英十分强调“名”的重要性,举证如下: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名者,人治之大者也,无可慎乎?
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
用一之道,以名为首,名正物定,名倚物徙。故圣人执一以静,使名自命,令事自定。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说文解字》为“名”释义,“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这里道出“名”的初始功能,即天黑时通过“自呼其名”来帮助对方确认身份。名,是个体的身份标识,也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代码,故给万物定名是认识世界的起点。
讨论动物命名,首先需要对“动物”进行概念界定。在古人观念和认知体系中,奇禽怪兽及以精怪和祥瑞为代表的“异物”是真实存在的,它们同样需要被辨识、命名、描述并加以利用。因而中国古代语境中的“动物”不仅指真实的动物,神化动物或虚构的“异物”同样涵括在内。
1.“其名自号”:象音命名法
《山海经·南山经》记载“有鸟焉,其状如鸱而人手,其音如痹,其名曰鴸,其名自号也”,“有鸟焉,其状如,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名自号也”,另《山海经·西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以上摘录三例句式相同,均是“有鸟焉……其状如……其名自号也”的形式。《山海经》中对动物进行描摹时有大量类似表达,“其名自号”有时亦作“其鸣自訆”“其名自詨”等,认为动物发声即是自呼其名。
清人陆以湉早已发现《山海经》中动物“自呼其名”频繁出现,在其随笔集《冷庐杂识》中就此评述,“鸟兽自呼其名,见于《山海经》者甚多,皆非世所常有……原其始,人特因其鸣声而命以名,后遂以为能自呼其名。凡禽言如布谷、脱布裤等,皆若是也”。所谓动物自呼其名,推其根本在于人最初是依据鸣声为动物命名。
《山海经》中对动物的描绘顺序符合人们认识动物的一般步骤,首先是观其形,然后再辨其音。若是创造用于书写交流的文字,最初必然与“形”密不可分,故而有“书画同源”之说。但文字毕竟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语言的出现比文字要早得多,只要有交际需求,就会形成语言,而语言则与“音”相辅相成。在文字尚未形成的远古时期,人们对声音更为敏感,类比于造字的象形法,这种以音命名的方法也可称为“象音法”。
《山海经》中还有不少动物采用叠名的方式,如从从、狪狪、鮯鮯、精精、蛮蛮、峳峳、朏朏、文文等,有的虽未明确言及“其名自号”或“自呼其名”,但推测这些动物名可能也是根据鸣声而来。
《荆楚岁时记》《异物志》《古今注》等作品中也提及动物“自呼其名”。布谷鸟也叫获谷鸟,《荆楚岁时记》中明确指出其名乃从鸟鸣之声而来,“四月也,有鸟名获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杷上岸”,“获谷”得名非常巧妙,兼备音义。再比如鹧鸪,《古今注》卷中“南山有鸟名鹧鸪,自呼其名。常向日而飞,畏霜露,早晓稀出,有时夜飞,飞则以树叶覆背”,又《太平御览》引《异物志》“鹧鸪,其形似雌鸡。其志怀南,不思北。其名自呼。飞但南,不北。其肉肥美宜炙,可以饮酒为诸膳也”,说明鹧鸪亦是因音得名。
“自呼其名”不仅仅是一种动物命名的方式,有时也可能作为增强知识可信度及权威性的“话术”,体现命名者驾驭宇宙万物之大道。韩非子在《扬权》和《主道》中均表达了“令名自命”的观点,“故虚静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焉”,意为圣人君主应把握宇宙万物运行规律,以虚静持正的至简状态使各物能各得其所、运行不悖。在其他早期文献中能够看到不少类似说法,这些与道家无为和儒家名实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求名称与事物本质相符合,才能“名正言顺”,达到理想之治。曹峰在讨论“执道者”与“名”的关系时,精辟地指出,作为塑造现实秩序的“命名者”应该保持与“道”相应的“无形”立场,这样才能超越秩序,以不变的姿态掌控时刻流动变化的世间万物。动物自呼其名、自报家门,命名者无须另立他名,只要随从即可。
要言之,“其名自呼”“其名自定”可作两个层面的理解:第一,体现原始朴素的动物“象音”命名法;第二,包蕴以虚静之道驾驭宇宙及人事秩序的治理之道。在一些文人墨客的诗文中,描绘动物“自呼其名”也透露出追求恬淡自然的心境,如宋之问《陆浑山庄》云“归来物外情,负杖阅岩耕。源水看花入,幽林采药行。野人相问姓,山鸟自呼名。去去独吾乐,无能愧此生”,即是。
2.会意命名法
有些动物名与鸣声毫无关联,试举两例:“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诸怀,其音如鸣雁,是食人”;“有兽焉,其状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诸,见则其邑大水”。无论是“怀诸”还是“夫诸”,似乎都看不出与动物发声的联系,亦不知其命名所据。对于那些大量目前已不知命名缘由的动物,不妨暂时先搁置处理,否则极易陷入“牛为什么名牛,蛇为什么名蛇”这样的无解之局。
除“象音法”外,不少动物的命名方式仍有规律可循,即把动物的某一特点抽离出来作为定名的根据,或可将此种方法称之为“会意命名法”。如果说象音命名法展现的是早期先民识物命名时较为原始朴素的状态,那么会意命名法则是动物知识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看到该动物名时能迅速在脑海中浮现其大致形貌。如为人熟知的啄木鸟,就是典型以会意法命名的。
郦道元《水经注》中提到“(沔)水中有物如三四岁小儿,鳞甲如鲮鲤,射之不可入。七八月中,好在碛上自曝,䣛头似虎,掌爪常没水中,出䣛头,小儿不知,欲取弄戏,便杀人……名为水虎者也”,生活在水中且像虎一样凶猛伤人之物命名为“水虎”,十分形象地点出动物的生活区域及性情特点。类似例子在《山海经》中亦能见到,“有兽焉,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飞,其名曰飞鼠”,“飞鼠”这一命名很好地凸显了动物外形像鼠且会飞的特征,容易识别记忆。
南朝刘敬叔《异苑》中有名为“叩头虫”者,“有小虫形色如大豆,咒令叩头,又咒令吐血,皆从所教。如似请放,稽颡辄七十而有声,故俗呼为叩头虫也”。《异苑》为志怪文本,所录带有神异色彩,可能其原型就是现实中一种常做磕头动作的虫类,俗称叩头虫,也名磕头虫,据《大辞海》,该虫前胸腹板的突出部分嵌在中胸腹板上,若将此虫放置木板上,用手指按住腹部,即以头和前胸击打木板,状如叩头,故名。
《酉阳杂俎》为唐代段成式所作,该书内容涵盖天文地理、仙佛鬼怪、动植矿生、珍奇异宝和宫廷秘闻等,包罗大量隐秘知识,其中亦记录不少以会意法命名的动物,如吐绶鸟、嗽金鸟、背明鸟、马头鱼、羊头鱼、印鱼、飞鱼、千人捏、冷蛇等,无须过多解释说明,仅通过名称便能直接把握动物的核心特征。
还有一类动物命名源于人事传说,若熟悉相关事迹,就较易理解该动物得名由来,故也将此类动物命名方法归入“会意法”。《博物志》中载有一种鱼名为“吴王脍余”,其得名与吴王有关:“吴王江行食鲙有余,弃于中流,化为鱼。今鱼中有名吴王鲙余者,长数寸,大者如箸,犹有鲙形。”相传吴王阖闾在行船宴饮时,将吃剩的鱼肉与残骨弃入江中,这些残骸化为鱼,命名“脍余”,《搜神记》称此鱼为“余腹”,大概即今日之银鱼。
再有《博物志》《异苑》《水经注》等书中均提到一种较为特别的老鼠,名“唐鼠”:
唐鼠形如鼠,稍长,青黑色,腹边有余物如肠,时亦污落。亦名易肠鼠。昔仙人唐昉拔宅升天,鸡犬皆去,唯鼠坠下死,而肠出数寸,三年易之,俗呼为唐鼠,城固川中有之。
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成固人也,学道得仙,入云台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鸡鸣天上,狗吠云中,惟以鼠恶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肠胃更生,故时人谓之唐鼠也。
该鼠有二名,一为易肠鼠,因为其腹边有余物如肠,时常污落,故名;一名为唐鼠,显然是从唐昉升天的故事而来,“唐”取自人名“唐昉”。无论得名源自外形特征还是传说故事,均是会意命名法之具体表现。
上述提出的动物命名之“象音法”“会意法”,实与认识事物一般顺序中的闻其声、知其理相合。那么,作为认识世界第一步的“观其形”,在命名中是否存在“象形法”与之对应?
容庚先生在谈到甲骨文中的动物象形字时明确指出:“羊角像其曲,鹿角像其歧,象像其长鼻……因物赋形,恍若与图画无异。”诸如羊、鹿、象、马、鸟、龙、龟等字,明显取自动物外形,可否将其看作以形为动物命名?笔者以为,在远古社会,语言交流是必要条件,但文字则非必要,语言先于文字产生,先有动物之名,然后可能有依据动物之形而造的字。虽然文字中有动物象形字,但创造文字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命名行为,二者并不存在必然关联,故不宜将“象形”单独作为一种命名方法。
需补充说明的是,我们在追寻动物命名规律时所使用的诸如《山海经》《异物志》或《酉阳杂俎》之类的文本,均是带有某些虚构性质的内容,这也意味着绝大多数“真实性”动物命名之由已无从得知,反而是在庞大的动物知识世界中处于边缘的、其真实性无考的“半虚构性”动物,可以发现一些命名规律的线索。
二、名称之不确定性:动物“同名异实”与“同实异名”现象
命名是人们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开始,但事物名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空之转移、认识之深化,名称也在不断演化,正因为如此,在古代文献中,会经常出现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现象。
古人特别重视对名物词的学习,孔子要求弟子“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尔雅》作为辞书之祖,收集和整理了2300多条名物词,其19篇中,与动物有关者占5篇,为《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在这些篇目中,动物同名异实和同实异名现象十分普遍。
先看同名异实的情况:
魾:《释鱼》“魾,大鳠,小者鮡”;《释鱼》“鲂,魾”。
鵅:《释鸟》“鵅,鵋䳢”;《释鸟》“鵅,乌鸔”。
皇:《释鸟》“鶠。凤。其雌皇”;《释鸟》“皇,黄鸟”。
所谓“同名异实”指的是不同事物共享相同名称,如以上简单摘举“魾”“鵅”“皇”等,同一名称之下可表示不同动物,不过这些名号虽指代具体对象有别,但均属同一类,相隔尚不算太远。
《尔雅》中还存在跨越类别之间的同名异实,《尔雅·释草》有“果臝之实,栝楼”,郭璞注“今齐人呼之为天瓜”,这里的果臝为一种蔓生植物,成熟的果实呈圆形;又《尔雅·释虫》“果蠃,蒲庐”,郭璞注“即细腰蜂也,俗呼为翳翁”,此处的果蠃则指头部呈球状的细腰蜂。清代学者程瑶田考察200余种名为“果臝”的事物后,完成《果臝转语记》一书,他精当地指出“果臝”一物“同名异实”是因以形相近,都有着似圆的外形特征,所以“肖物形而名之,非一物之专名”,“虽妇人孺子,见物之果臝然者,皆知以果臝呼之”。
另如《尔雅·释草》“茨,蒺藜”,郭璞注“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可见蒺藜是果实表面带有三角状刺的蔓草;而《释虫》“蒺藜,蝍蛆”,邢昺疏“《广雅》云‘蝍蛆,蜈蚣也’”,蜈蚣体长多足,有能够射出毒液的颚爪刺人。茨草带刺与蜈蚣多足刺人在事理上相近,故都被称为“蒺藜”。
程瑶田在论及同名异实问题时,指出“诸物称名相同,‘或以形似,或以气同’”。简言之,造成不同事物共名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因外形相似而同名,一是因事理相近而同名,王引之曾言“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即是此理。命名最重要之依据是事物的性质特征,而某些事物的特征又具有相似性,因而人们会习惯性将具有相似特点的事物联系起来,赋予相同名称。
再看同实异名,即相同事物拥有不同名称。前文论及事物特征是命名的重要依据,但事物个性复杂多样,正如盲人摸象,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之人关注或认识的事物特征不尽相同,导致同实异名的产生。
王国维先生在《〈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中写道:
物名有雅俗,有古今。《尔雅》一书,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谓之“释”。释雅以俗,释古以今。闻雅名而不知者,知其俗名,斯知雅矣。闻古名而不知者,知其今名,斯知古矣。若雅俗、古今同名,或此有而彼无者,名不足以相释,则以其形释之。草、木、虫、鱼、鸟多异名;兽与畜罕异名,故释以形。凡雅俗、古今之名,或同实而异名,或异实而同名。
其指出事物同实异名的原因有二,一为雅俗之差,一为古今之别。《尔雅·释虫》“蚬,缢女”,郭璞注:“小黑虫,赤头,喜自经死,故曰缢女。”“蚬”即为蝶蛹,身长一寸左右,体色黑,头部为红色,性喜吐丝,悬挂空中如同自缢一般,故又名“缢女”。“蚬”是雅名,“缢女”是俗称,后者较前者更为通俗显意。再《尔雅·释鸟》“䴕,斲木”,郭璞注:“口如锥,长数寸,长斲树食虫,因名云。”䴕与裂字同源,均有割裂之义,“䴕”即啄木鸟,亦是雅名与俗名之别。郭璞在《尔雅》注中常用“某某,俗呼某某”的句式,如“(蜩)俗呼为胡蝉”“(鱊鮬)似鲋子而黑,俗呼为鱼婢”“(鶨)俗呼为痴鸟”等,即是对雅名和俗名的区分。
除雅俗外,亦有古今之别,不过因不少古籍成书具体年代不易准确判断,事物名称出现先后亦不易把握,故选取例证相对困难,在此仅以一例加以说明。
《博物志》载“东海有物,状如凝血,从广数尺,方员,名曰鲊鱼,无头目处所,内无藏,众虾附之,随其东西。人煮食之”,此处“鲊鱼”其实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水母”和“海蜇”,历史上,“水母”名出现较早,“海蜇”相对晚出。唐代段公路《北户录》中专有“水母”一条:
水母,《兼名苑》云:“一名蚱,一名石镜。南人治而食之,云性热,偏疗河鱼疾也。其法先以草木灰退去外肉,中有一物或紫或白,合油水再三洗之,杂以山姜荳蔻煮过,其莹彻不可名状。至于真珠紫玉,无以比方此物。须以虾醋食之,盖相宜也。”……《稽圣赋》云:“水母,东海谓之。正白蒙蒙如沫,生物皆别无眼耳,故不知避人。常有虾依随之,虾见人惊,此物亦随之而惊,以虾为目自卫也。亦如视肉有眼,以物摘之,则其眼移处。”
水母是海洋中常见的浮游生物,据《博物志》《稽圣赋》《北户录》《兼名苑》等中古时期文献记载可知,当时已有“水母”之名,亦被称为石镜、鲊,鲊或写作“蚱”或“䖳”等,无目,可以食用,《兼名苑》载有详细的食用方法。
及宋以降,“海蜇”名频繁出现,如苏轼文集中“茄柴灰可淹海蛰(蜇)”一句,至少说明当时已有“海蜇”之称。元代有一首诗名为《海蜇》:“层涛拥沫缀虾行,水母会秋孕地灵。海气冻凝红玉脆,天风寒结紫云腥。霞衣褪色冰涎滑,琼缕烹香酒力醒。应是楚江萍实老,误随潮汐落沧溟。”全诗以“海蜇”为名,且在诗中另用“水母”一词,可知两者为一物。王夫之《说文广义》中提到“鮺”时,说当时将“鮺”俗作“鲊”有误,并强调“说文无‘鲊’字,后世有此字,音诈,今之海蜇”。
那么,“水母”与“海蜇”是如何得名的呢?清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提供了线索:
水母,生海中,以咸水之渣滓为母,故名水母。鲜煮之辄消释出水。一名海,气最腥。为虫之所宅,虫者虾也。水母以虾为浮沉,故曰水母目虾。性冷,能化物,不能自化,脾胃弱者勿食。干者曰海蜇。腹下有脚纷纭,名曰蜇花。八月间干者肉厚而脆,名八月子,尤美。
其认为取名“水母”乃因该生物以咸水渣滓而生,即以咸水为母之义;而名为“海蜇”的原因是其腹下有脚,《说文·虫部》“蜇,虫行毒也”,海蜇多触角,刺人且有毒,与“蜇”之义吻合,又因生活在海水中,故名“海蜇”。不过这一材料时间上与中古相距甚远,暂放于此,聊备一说。“水母”与“海蜇”,取自生物之习性特征不同,名称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二者并未构成完全的替代关系,或者说,海蜇是水母一分支,至今两名称都仍在被使用。
除雅俗、古今外,造成动物同实异名的还有方言因素,为使讨论更为集中,选取《方言》一书作为核心文本。《方言》又名《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传为西汉扬雄所撰,是目前所存第一部比较各地方言的著作。该书方言涵盖地域范围较广,东起海岱,西至秦陇,北起燕赵,东北至朝鲜洌水,南达南楚。今本《方言》为郭璞注本,凡13卷,其中卷八和卷十一为动物方言词汇,据笔者统计共35条。
这些因方言导致“同实异名”的情况较为复杂,简单来说大致可分三类:一是语转造成,如“蝇”,在秦晋和江东一代被呼为“羊”;又或布谷与获谷,亦是音近。二是选取动物特征不同,如“䳚鴠”,周魏齐宋之间谓之“独舂”,乃因该鸟“好自低仰”;自关而东谓之“城旦”,是“言其辛苦有似于罪谪者”;或被称为“倒悬”,是因其“好自悬于树也”。再如“蝙蝠”,自关而东谓之服翼,“服”有时也可写作“伏”,取其昼伏有翼之义;或被称为“飞鼠”,则是因其形似老鼠而会飞之故。第三类是各地取名既无发音亦无意义上的联系,完全是因各地域相互独立对某一动物命名而造成的差异。
此外,郭璞注中补充了许多动物在江东或江南的方言名,“雁,今江东通呼为鴚”“蝉,江南呼螗蛦”“螳螂,江东呼为石蜋,又名龁肬”等。据《晋书·郭璞传》,郭璞为两晋时人,永嘉之乱时,南下避祸,后活动于江南一带,故其在注《尔雅》和《方言》时,都特意强调了物种在江东、江南地区的名称。
总而言之,历史上的动物名称会受三重维度影响,即纵向的时间因素、横向的地域因素及书面或口语等使用场合因素。如此便造成了动物名称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是伴随着不同条件自然发生,甚至无法避免。
三、解经与日用:两套动物命名系统
起初因认知水平较低,人们对动物的辨识处于混沌状态,随着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走出原先质朴的命名方式,对事物做出细致区分,不过似乎很快又走入“另一极端”:几乎每一事物都有独一无二的名字。
《鲁颂·駧》中提及许多马名,如驈、骓、駓、骍、骐等,根据《毛诗正义》可知,这些字表示毛色不同的马。类似情形在《说文解字》中有集中体现,《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作者许慎是东汉著名经学家,其考辨汉字源流,对汉字之形、音、义进行整理并加以规范,书中保存了丰富的动物资料。与上引“马”的例子相似,在《说文解字》的“牛部”“隹部”“羊部”“鸟部”“乌部”“豕部”“豸部”“马部”“鹿部”“犬部”“鼠部”“鱼部”“虫部”中,按动物颜色、体貌、年岁、习性之不同,同一种动物之下各拟专名。摘取“牛部”部分内容,如牡为公牛,牝为母牛,犊为牛子,㸬为两岁牛,犙为三岁牛,牭为四岁牛,牻为黑白相间的牛等。
再以蝉为例,《方言》载“其大者谓之蟧,或谓之蝒马;其小者谓之麦蚻,有文者谓之蜻蜻,其蜻谓之尐,大而黑者谓之䗃,黑而赤者谓之蜺。在《尔雅》与《广雅》的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篇目中,相似例证俯拾皆是。
为何古人会不厌其烦地对事物进行细致区分并单独命名?要注意到,《诗经》《尔雅》等为儒家经典文本,作《方言》的扬雄、作《说文解字》的许慎均为研习经传之大师。换言之,这套为万物分别命名的理念主要存于知识精英中,此与儒家“正名”思想密切相关。
孔子强调以“名”为核心构建社会运行的基本准则,并通过“正名”达到知礼与卫道的目标。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明确提出“正名主义”一词,认为“他(孔子)的中心问题,只是要建设一种公认的是非真伪的标准。建设下手的方法便是‘正名’。这是儒家公有的中心问题”。《尚书·吕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礼记·祭法》“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对儒家而言,命名、定名、正名是不言自明的。
对于“正名”思想,历来有不同理解,大体从“形名”“名实”“名字”“名分”等角度入手。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将“正名”思想归纳为两个层次:一是正形名,即对自然、社会和一般事物的客观历史观察,做出别同异、辨真伪的“事实判断”;二是正名分,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意义,通过定名正理平治,做出明贵贱、别善恶的“价值判断”。
“正名”思想中所涵括的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并非割裂,一般而言,将“正名”理念等同“名分”,侧重其高低贵贱政治伦理方面的情形较多。但就本文讨论的动物命名问题而言,其知识性“正形名”的指向更强,《尹文子》云“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以名正形,使名实相副,此乃“大道”。从认识论角度,或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上述“复杂化”的命名方式。
第一,万事万物皆当有名,名定而后才可对事物进行辨别、归类,“名”是区分各物最核心的要素,是建立秩序的开始。正如在茫茫宇宙中发现某颗小行星后为其冠上“专属名”,人对万物命名的兴趣还源于内心朴素的“探险家”本质,不放过任何一个细微事物,并为其贴上“人为”的标签,从而展现对自然和宇宙的征服与控制。
第二,“博物”是儒家重要理念之一。侯外庐认为,孔子正名思想以“知”和“学”为核心,只有“博学”才能“贤德”。“博物”即博学多识,孔子劝说学生读《诗》,就是因其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博学之士备受推崇,班固称“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对万物进行细致辨析、分别命名并加以解释,正与儒家的博物多识传统相合。
第三,汉代经学占据主流,解经盛行,训诂之学备受重视。无论是许慎的《说文解字》,还是时代稍后的郭璞注《尔雅》、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其主要目的乃为解读儒家经典服务。《说文解字》虽为一部字书,但在释字的同时也承担了辨物命名的功能。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表明其创作初衷,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中进一步明确该书旨在正本清源,针对当时“巧说衺辞”进行解谬,从而“晓学者,达神恉”,使人不疑,进而使天下不乱,以达王政之治。对事物进行繁复的命名和释名行为,恰与这样的经学背景有着紧密关联,其目的是为解经扫除障碍,并不是服务于日常。
无论如何,对事物做出细致区分并单独命名,表现了古人早已走出原始的混沌状态,思维方式趋于清晰化。但正因这套知识根植于特定的学术土壤,并不适用于日常生活,几乎仅存于知识精英中,注定其必然走向衰亡。以《说文解字》为例,有学者统计,其346个与五畜相关的字绝大多数已成为“死字”,常用字不足10%。
与“精英化”相比,“日用性”的动物名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一问题,或可用“字书”“辞书”这类材料进行讨论。目前利用“字书”进行的研究非常缺乏,黄德宽、常森就对人们忽视汉字与文化传统的深层关系深表忧虑,认为目前汉字研究“并未清醒地认识、理解文化传统在汉字发生、发展、构造、认识、价值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字词的演进在历史中会受到诸多方面影响,如外来词、流行语对字词的丰富,表达习惯之变异而对字词的改造等,通过比对不同时期常用字词之不同,或可找到打开社会知识变化图景的密码。
与《尔雅》《说文解字》《方言》《广雅》《玉篇》等“精英化”的字书相比,至迟到唐代出现了不少面向普通民众的常用字词书。敦煌出土写本中存有大量字书,朱凤玉将其分为6类共13种。动物资料相对集中者,以《俗务要名林》和《杂集时用要字》(四)两份为佳。
《俗务要名林》是一部分类辑录通俗常用语的唐代字书,共分甲、乙卷两个抄本,甲卷由P.5001、P.5579、S.617三写卷缀合而成,乙卷为P.2609。其中所收录的词汇按义类分为田农部、珍宝部、菓子部、菜蔬部、酒部、饮食部、杂畜部、兽部、鸟部、虫部、鱼鳖部、木部、车部等,生动地反映了中古社会生活。据《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的释文,笔者整理《俗务要名林》中动物部分,统计得出《杂畜部》中动物名38种,《兽部》中动物名29种,《鸟部》中动物名31种,《虫部》中动物名43种,《鱼鳖部》中动物名39种,合计共180种。
《说文解字》与五畜相关的字合计346个,鸟类相关字222个,鱼鳖类相关字113个,还有大量尚未统计的虫类和兽类名字,而《俗务要名林》中展示的民间常用动物名则大为简化,字书编撰之目的由此前解经转向服务生活。
与两汉时期相比,唐代俗用动物名多以某+“子”或某+“儿”的形式,如蚊子、蠓子、蛹子、子、猫儿等。根据时代稍晚即唐末五代时期的敦煌写卷S.3836《杂集时用要字》(四),可知以名词+“子”“儿”等后缀,或名词+“老”等前缀是中古时民间呼唤常见动物的惯用方式。该写卷残损较为严重,不过目前存留部分有不少动物名,在此有限的篇幅中仍可见诸如雀儿、老、骆驼儿、马驹儿、狢子、獚儿、老鼠、师(狮)子等当时普遍流行的动物名称。
虽然不知《俗务要名林》与现被定名为《杂集时用要字》(四)的作者为何人,判断很有可能就是当时民间知识分子,但这两份材料汇集的俗用字词,为我们展示了潜藏在精英化动物知识之外日用性动物知识的丰富性。这也意味着,精英思想与一般性知识虽有分流,但并非分道扬镳:一方面,精英知识需要通过种种手段渗透民间以增强其影响力;另一方面,一般知识也为精英人士提供思想资源,显示了知识的流动性。
为思想齐整也好,为解惑也罢,“圣人君子们”为动物命名之实质乃是对于“确定性”的追求,但时空流转之下的民间知识无时无刻不在挑战这一“权威”,溢出“确定”的边界而造成知识的“不确定性”。正是“确定”与“不确定”间的不断角力,表明文化和知识的生成与发展具有相当的弹性空间,具有多元而复杂的面向。
如果说字书编修工作是对知识的整合,那么其编撰目的从汉代解经之需到唐代民间之用,便反映出中古时期动物知识生成的两种不同旨趣。因目的不同,一个“求全”,一个“求常”,故所搜罗动物名的范围亦有显著区别。与精英知识的相对稳定性对比,民间的一般知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变化反应较为灵敏,如中古时期动物名称中出现的“子”“儿”“老”等缀语,即鲜活地勾勒出当时动物知识出现的新动向。
余 论
以往学界在讨论动物命名问题时,多从“辨名劾物”的巫术层面理解,事实上,“名”所具备的巫术意味并非动物所特有,因而这种研究模式或“套路”往往忽略了动物本身的生物属性及特质。相较于其他事物,动物深刻“介入”人类生活,在历史进程中,人与动物彼此塑造、协同演进,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介入”,使得动物论题变得异常复杂。历史从业者习惯于条分缕析,从纷繁中理出脉络,但需警惕过度地“简化”对历史本身复杂性的遮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