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AI项目,如何做到真正以儿童为中心?
下面这两个引人深思的故事都发生在博物馆中,有关于儿童、青少年与AI的关系。这两个故事揭示了博物馆在遇到AI时所面临的挑战,也提醒我们博物馆专业人员:在工作中,我们应当采取既批判又开放的方式对待AI,不能将它简单化或是一概而论。
在第一个故事中,一位母亲急匆匆地要求与一位科技馆馆长见面,她告诉馆长,自己的儿子在几周前突然和她说,他只会和私人聊天机器人互动,因为那是他唯一信任的人。孩子的话让这位母亲感到很绝望,不知所措,所以只好向馆长求助。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一场博物馆的儿童工作坊中。一群孩子本应按照引导,用DALL·E软件生成的图像创建一个虚拟花园。但出人意料的是,孩子们拒绝遵循工作坊规定的流程。他们认为AI生成的图像枯燥又乏味,而自己脑海中想象的图像可要比这些好太多了。于是,孩子们立即向工作人员要来了纸和彩铅,自己动手画了起来。

那么,我们在博物馆中究竟要怎样运用AI工具与儿童互动呢?我们使用AI,仅仅因为它是必然趋势吗?还是因为AI看起来很酷,可以让博物馆看起来“与时俱进”?因为AI未来会持续发展,所以我们越早接受它就越好?
在这场科技狂潮中,有些人会迷失方向,他们会因盲目追随最新的科技成果,而压制甚至完全忽视儿童和年轻人的想法。正如我们之前对AR、VR、元宇宙等技术的盲目追求的时候一样,孩子们总是缺席其中。我们自以为了解他们,认为能够用这些技术吸引到他们,但前面的两个故事已经在提醒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为儿童设计AI项目,盲目地探讨他们与AI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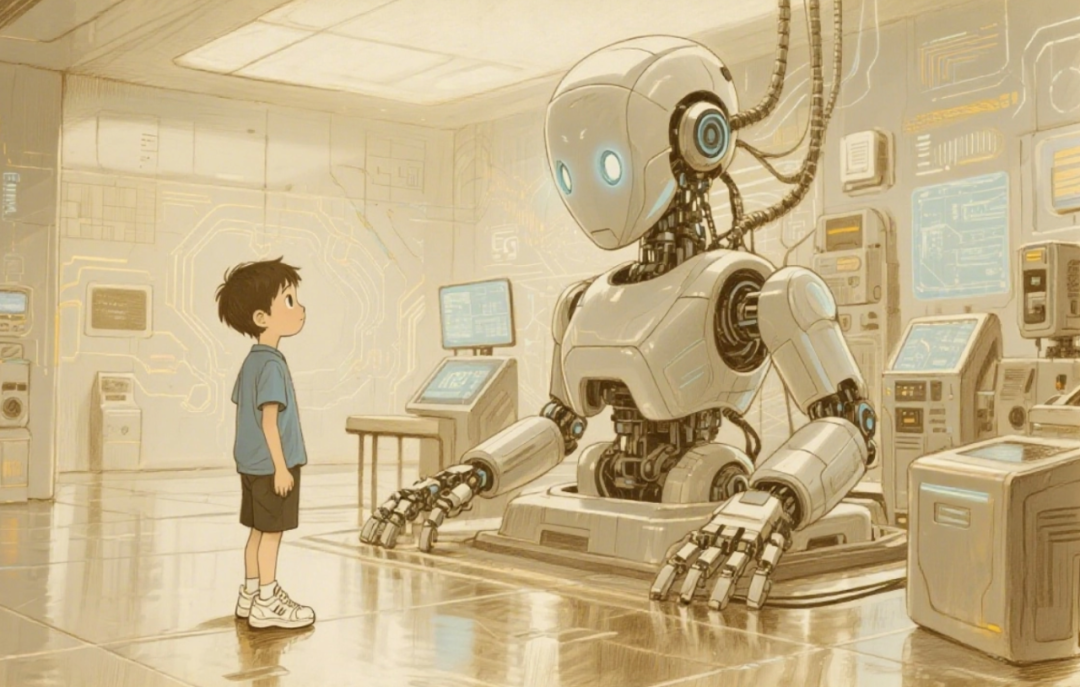
所以,不如让我们从最基础的事情开始:
我们有认真问过孩子们对AI的看法吗?
我们知道他们在家怎样与Siri、Alexa、Cortana互动吗?
对于生活被疫情严重影响的一代来说,AI是如何发挥安慰剂作用的?
孩子们对AI是感兴趣更多,还是担忧更多?
AI是否符合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孩子们的需求、最关注的事、面对的挑战和期望分别是什么?
在谈论“儿童与AI”之前,或许我们应当先做的是听见他们的声音。
在博物馆中面向儿童和年轻人引入AI工具,潜藏着一个关键风险:它可能会重现那些基于创收逻辑的偏见和知识结构(以及由此产生的权力)。这是所谓的“黑箱技术”,我们不清楚它是怎么运作的,也无法改变或重新调整它。
正因如此,一些团体提出了改变这种模式的建议。例如Polina Lulu和Yesim Kunter带领的AI for Kids UX,以及Cultural Inquiry与瑞士东部应用科技大学、Collaboratio Helvetica合作开展的项目。项目提倡首先要倾听孩子的声音,思考他们的想法,然后启动一个由孩子引领的共创流程。有趣的是,AI会在整个流程的后期才开始介入,最主要的技术是倾听、深度观察、语言、同理心、游戏和讲故事。
我们需要先摒弃AI,继而创造一种源自儿童、以儿童为中心的新型AI。这种新型AI应该允许孩子玩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与AI的互动总是这么严肃和无聊。它应该更好地回应孩子的社交需求,鼓励他们认同自己的多样性,帮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提升自尊并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们建立更深的连接而不是制造依恋障碍。新型AI应该能够帮助孩子们避免陷入社交媒体每天精心散播的仇恨和恐惧陷阱中,让他们能够忠于自己的梦想,而不是限制或扭曲他们的梦想。新型AI应该帮助博物馆与孩子的生活产生共鸣,丰富他们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变得琐碎和肤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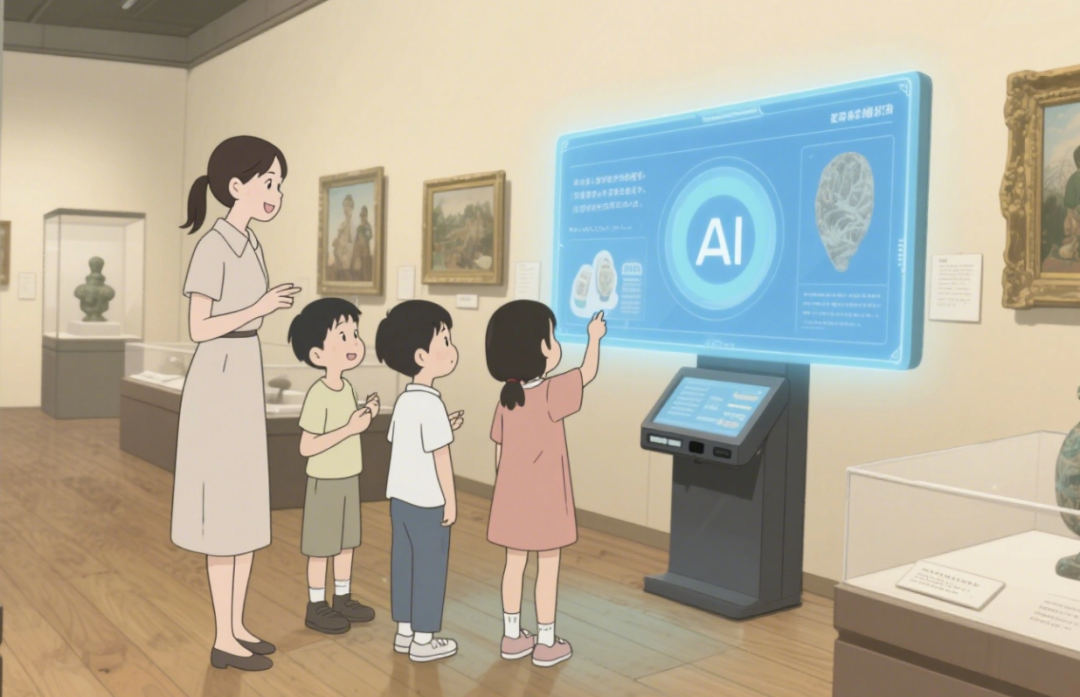
博物馆有能力帮助孩子们重新定位AI在生活中的位置,这关系到孩子们的心理健康、社会关系,以及他们和博物馆的未来。
因此,当我们想使用AI工具创造内容时,不妨先想想自己拥有什么。想要找到真正的答案,我们不需要去问ChatGPT,而应该去问那些来访的渴望表达的孩子和年轻人。这对博物馆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契机,也许未来AI会变成孩子们进入博物馆后的首选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