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一个超越尘世的诗意空间——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熏炉

镂空云龙纹青铜豆形熏炉 黄喆安琪/摄
中国古代熏香文化有数千年的历史。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出土的镂空形器,是中国早期熏香器皿的雏形。形制较为成熟的熏炉,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逐渐流行。而汉墓考古发现所见材质各异、造型不一的熏炉的大量出现,也从侧面见证着熏香文化在汉代的盛行。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造型繁复、工艺精绝的各式青铜熏炉15件,对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熏炉做形制与装饰工艺的分析,并探寻其功用与造型美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做造物思想、社会信仰等更深层次的精神文明的相关探讨,将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汉贵族等级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及造物艺术背后的汉代社会历史文化。
在熏炉里放香料,下置炭火,上覆云母片或银叶,再放草本类香料,低温慢焙,或将树脂类香料如乳香,切碎后焚烧。这两种方式可从炉盖的镂空中散发出袅袅香烟。熏香功用,在于去除室内异味,净化空气,或熏烤衣物,驱虫防蛀,或祛除卑湿,治疗疾病。从西周时期起,熏香还常见于礼乐宴飨等贵族娱乐生活场景中,人们在香料熏蒸带来的朱火青烟和香气激起的陶醉愉悦氛围中,构建出一个超越尘世的诗意空间。
一、青铜熏炉的功用
(一)净化空气,驱避蚊虫
相较于现代社会的烟尘污染,秦汉时期的空气显然更清新,但“清洁居室空气环境仍然是秦汉人尤其是贵族阶层重视的生活内容”。汉代青铜熏炉使用的香料基本可分两大类:兰草、艾草、柏木、桂皮、花椒等本土香料,沉香、檀香、龙涎香、乳香等外来香料。熏香是通过熏蒸,散发香料的挥发性成分,达到去除异味、净化空气的功效。《博物志》载汉代宫廷曾燃烧贡香,净气疗疫,“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十余日,香由不歇”,可见熏香净化空气之强效。
汉代人对驱避蚊虫也有消杀方式。“汉代防避蚊子的主要方法是烧艾蒿熏”,海昏侯国地处鄱阳湖平原,河网密布,水草丰茂,蚊虫较多,周边湿地也为艾草提供了天然生长区。海昏侯墓出土的15件青铜熏炉是对抗“湿瘴”与蚊患的刚需。
(二)熏蒸衣被,防霉留香
通过香料燃烧的烟雾熏染织物,既可防潮防霉,又能赋予衣被持久香气,这一习俗盛行于汉代贵族阶层,形成一套熏染技术。南方潮湿环境下,熏炉热量与香料(如沉香、柏木)的干燥作用可抑制霉菌滋生,适用于储存贵重的锦、绣、罗等织物。
《后汉书》载汉明帝“诏太官赐尚书以下朝夕餐,给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注引蔡质《汉官仪》:“尚书郎入直台中,官供新青缣白绫被,或锦被……女侍史洁被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中,给使护衣服。”意思是尚书郎的女侍史负责清洁被褥衣物,手持香炉焚香熏蒸,随行进入尚书台,供职差遣并保管护理衣物。也就是说,汉代官员的衣物普遍使用熏香进行防蛀、祛味、留香处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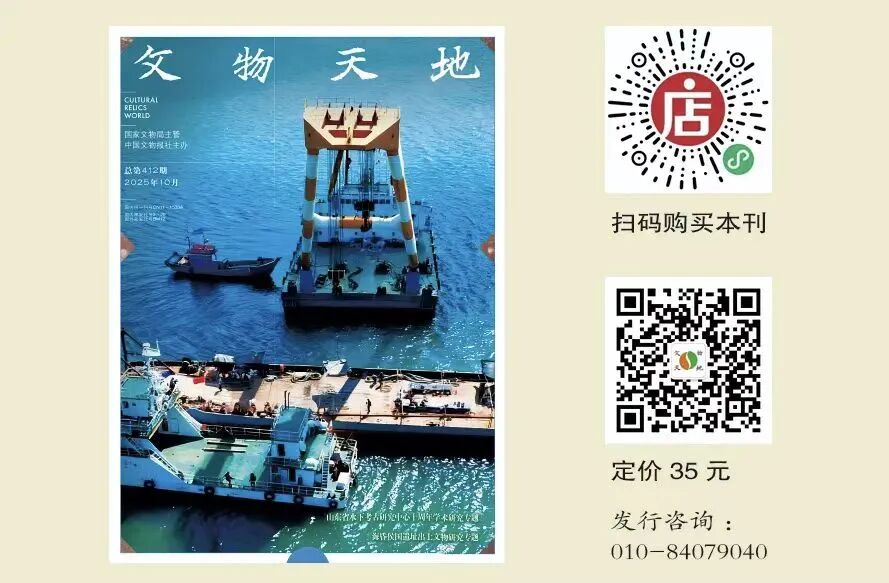
(三)祛湿除邪,疗愈疾病
结合史料与出土熏炉实物研究,学者认为“西汉以来采用熏炉燃烧香料治疗疾病的方法已经较为成熟”。把外来树脂类香料(如苏合香、龙脑香)放入熏炉,通过炭火缓慢加热,促进其释放芳香分子,也被科学实证具有抗菌作用:现代研究证实,艾草烟熏可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减少呼吸道和皮肤软组织感染。汉代人无微生物概念,但已通过经验掌握其功效。
“在汉代,熏香的风气南方较北方为盛。比如广州发掘的400余座汉墓中,共出熏炉112件,自西汉晚期开始,近半数的墓葬中随葬熏炉;而在洛阳烧沟发掘的220余座汉墓中,仅出熏炉3件。可见两地的差异之大。”南方熏炉的使用之盛,与湿热的气候条件密切相关,《史记》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记述。刘贺出生成长于山东昌邑,人生的前30年生活在北方,受封海昏侯到江西南昌,受山阳太守张敞的严密监视,政治上的抑郁不得志,加之南方潮湿闷热的环境,使刘贺身体渐趋衰败。
学者研究认为,海昏侯刘贺“走向死亡之路的疾病,很可能是因风湿、风寒而引起的肢体不遂及肺、肾等方面的病症。”而海昏侯墓中出土大量的铜熏炉可能正是刘贺为治疗与防止疾病侵袭所做的准备。
(四)彰显身份,象征等级
“西汉时期,雕镂精美的铜博山香炉,开始出现在已被发掘的王公勋贵的坟墓之中。”青铜熏炉作为礼器与实用器的结合体,材质、装饰工艺及使用场景,均深刻体现了汉代社会的等级制度。

青铜博山炉 张冰/摄
从材质说,汉代时青铜逐渐从商周时期的主流礼器材质,转向日用器皿制作。但因采冶、铸造、雕刻等工艺复杂,加之朝廷限制地方采矿铸铜,重要金属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国有,民间私铸铜器困难,青铜器皿主要供给对象仍然是贵族阶层。与海昏侯墓时期相近的西汉中期诸侯王墓中,也可见各式青铜熏炉的身影: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线条极为活泼流畅的错金青铜博山炉、广州南越王墓出土四连体铜熏炉等。而墓主为普通官吏及其家属的洛阳烧沟汉墓群中,出土熏炉为泥质灰陶。可见,海昏侯墓出土的全部为青铜材质的熏炉,是墓主人身份的象征之一。
从装饰工艺言,海昏侯墓出土熏炉所使用的鎏金、透雕等复杂的高成本工艺也常见于贵族墓葬出土文物,与墓主身份等级相符。鎏金制品代表了使用者的财富水平,体现其对奢侈的追求导向。透雕工艺复杂且考验工匠技术,多用于制作玉器、青铜器等高档工艺品,其成品持有者通常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从使用场景说,汉代青铜熏炉的使用涵盖祭祀、宴饮、焚香阅读、室内起居、驱邪疗疾等不同场合,这其中绝大部分是贵族生活的日常。熏炉的制造与使用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同等级的贵族在持有熏炉的种类、数量、规格和装饰工艺及香料上都有明确差异,熏炉成为他们彰显身份地位、享受品质生活的重要物化表征。
(五)事死如生,陪葬器用
汉代丧葬讲究“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这种理念通过墓葬形制、陪葬器物和丧葬礼仪来实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厚葬体系。具体到墓葬的空间结构上,“汉家葬制……最大特征就是墓室高度居室化和宅院化。”海昏侯墓的布局陈设即高度模仿墓主人生前的宅院居室。其墓出土的青铜熏炉是“西汉大型墓葬中出土青铜熏炉数量最多、品种最丰富的一例,尤其是主椁室内8件,仿照日常生活中博山炉的使用方式摆放,为我们认识西汉博山炉的组合方式、使用场合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


带鋬青铜博山炉(带承盘、炉盖) 张冰/摄

带鋬青铜博山炉(无承盘、炉盖)张冰/摄
仿效墓主会客厅堂的刘贺主椁室西室内,出土1件青铜豆形熏炉和4件青铜博山炉,与青铜臼、杵及漆耳杯、漆盘同置漆案上,再现墓主人生前宴饮的日常;仿效墓主起居寝室的主椁室东室内,出土另1件青铜豆形熏炉和2件青铜博山炉,相伴出土“李姬家定”铭青铜豆形灯、鎏金青铜撮箕、玉具漆剑及龙凤螭纹蝶形佩等刘贺日常起居休息、装饰佩戴会使用到的器具,还原了西汉贵族的居室陈设。青铜熏炉与海昏侯墓数量庞大的其他陪葬器皿,在冥界侍奉墓主如同生前,为墓主营造了冥界的繁华生活。

鎏金青铜博山炉 张冰/摄
二、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熏炉与西汉造型美学
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熏炉不仅承载着实用功能,更以熏炉为媒介,将汉代器物审美和物质文明熔铸于方寸之间。
博山炉出现于西汉中期,逐渐成为青铜熏炉的主流造型。“西汉中期直至东汉后期,其他式样熏炉完全被博山炉取代。”海昏侯墓出土的青铜熏炉造型纹饰包含人物造型、动植物造型纹、抽象几何纹等类,细致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西汉造型美学。
(一)人物造型
人物造型在海昏侯墓出土青铜熏炉中最典型突出的莫过于人驭龙座青铜博山炉的人形底座。此人物半蹲骑的姿态,左手前推,右手擎灯,身形矫健,姿态生动,汉代“人驭龙”“人驭虎”图像较多出现在北方画像石中,较少见于铜熏炉上。同时期的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也出土一件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底座一力士屈膝骑坐在卧兽上,左手撑兽颈,右手擎炉身。兽跪卧昂首,张口欲噬。海昏侯墓出土的人驭龙座青铜博山炉与之相似,但“此型炉在长江以南地区是首次出土。”此人形可能为仙人或墓主象征,与蜿蜒的龙身整体形成“人龙共舞”的动态美感。

人驭龙形青铜博山炉 张冰/摄

西汉 鎏银骑兽人物博山炉 河北博物院
(二)动植物造型纹饰
2件青铜豆形熏炉整器饰凤鸟纹、螭虎纹,双层炉盖与炉身的外层主要纹饰为透雕云龙纹。13件青铜博山炉饰鹿、熊、虎、凤鸟、立龟、龙等动物造型纹饰,矫健的鹿昂首挺立,壮硕的熊罴攀援其间,威猛的螭虎蓄势待发,展翅的凤鸟翱翔云端,沉稳的立龟昂首向天,蜿蜒的游龙穿梭其中。

凤鸟立龟青铜博山炉 张冰/摄
植物造型纹方面,主要为博山纹、草叶纹等,“除仙人仙兽以外,西汉美术中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对‘仙山’或‘仙境’的表现”。镂雕工艺描绘出层峦叠嶂的山峰造型,正如汉代乐府诗中所描绘的“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以松柏,下根据铜盘”,这里“以”通“似”,形容铜炉炉盖上的博山纹似松柏枝。每当熏炉中燃起香料,镂孔中袅袅上升的烟气,让人产生拥有茂密森林的山间云雾蒸腾,乃至进入仙境的错觉。
(三)抽象几何纹饰
海昏侯墓出土熏炉中的抽象几何纹包括卷云纹、水波纹、弦纹等。卷云纹以流畅的弧线构成连续卷曲的云朵形态,形似空中翻卷的云气;水波纹翻涌交错,形似浪花翻腾,线条疏密有致;弦纹主要以宽带纹出现在熏炉腹部的口沿及炉腹中央位置,通过几何化的秩序感平衡繁复纹饰的视觉张力。
多种造型纹饰相组合,再辅之以镂雕、鎏金技艺,展现出汉代青铜铸造与装饰的精湛工艺,和西汉中期繁简并存、拟物象形、精工雕琢的造型美学。
